高考落榜,自学成才,34岁走上大学讲台;
痴迷党史,40年来跑遍全国各大城市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
考证文献,信仰的力量使红色史料“活起来”……
他就是304am永利集团二级教授田子渝。

秋尽冬来,雨后初晴的武汉已有阵阵凉意,街头金黄的银杏叶尽显浓烈与静谧之美。迎着初冬的暖阳,记者走访了这位红色史料的梳理者与传承者。
“有时一连几天,甚至更长时间,一无所获。偶尔发现一份新材料,得意忘形地手舞足蹈起来。”75岁的田子渝说,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新时代。早些年查资料很困难,只能在故纸堆里一本本翻阅。后来有了缩微胶片,现在很多图书馆、档案馆都已数字化,只要联网,在家里就能看各大图书馆的图书。身处国家澎湃进步的大时代,满头银发的田子渝,见证了历史文献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诸多进程,更为红色史料的挖掘与研究贡献了无限心力。
自小痴迷党史
田子渝,1946年出生于一个红色革命家庭。自幼就喜欢画画、读书,作文也写得好。在他书房的一个柜子里,整齐地摆放着以前的旧日记本。年少时,他曾经和几个同学相约,从武汉步行经过洪湖,途径韶山,一路走到了井冈山。在快到韶山的路上休息时,田子渝随手画了一幅傲雪红梅,至今还夹在日记本中。聊到这时,他饶有兴致地说,“给你看看我当时的画”。话未落音,他已起身快步走向书房。
1965年,田子渝高中毕业,却高考落榜。当时武汉市急需一批中学教师,挑选1000名单科成绩好的高中毕业生进行培训。由于语文成绩非常好,他被选送到武汉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967年,他被分配到武汉近郊的胜利中学教书。
“在中学,我一教就是10年。”田子渝对记者说。刚到学校,学生还没有复课,空余时间非常多,他手不释卷,嗜书如命。复课后,田子渝承担了语文、美术、音乐等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每天基本上10节课。繁重的教学工作外,他总能尽量挤出时间看书。当时,学校有个图书室,为了方便阅读,田子渝干脆自己保管钥匙。每到周末,他还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去武汉市图书馆翻阅文献、查阅资料。为节省午饭时间,用打点滴的玻璃瓶灌满水,带两个馒头,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成了田子渝周末生活的日常状态。
父母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信仰,深刻影响着田子渝,也是他自小就对党的革命历史非常着迷的重要原因。通过广泛阅读,他发现,董必武、李汉俊、恽代英、李大钊等党的革命先辈,很多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不仅是革命者,还是工程师、大学教授,生活条件优越,不是吃不饱、穿不暖迫不得已才干革命的。田子渝的心中不免产生了很多疑问:为什么他们要放弃美好的生活去推翻旧社会?干革命不仅没有钱,还有可能丢了性命,这该怎么解释?弄明白这些问题,促使他对党史的学习研究愈加深入。
破格评上副教授
阅读之余,田子渝尝试写文章。“当时只有武汉师范学院属于武汉市管,我贸然给《武汉师范学院学报》投了论文《沙俄在武汉的侵略罪证》,居然刊登了。”他记得,这篇处女作发表后,就收到了20元稿费,比照当时他的月薪30元,这着实是不小的惊喜。
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之际,33岁的田子渝撰写的《五四时期的武汉》一文,在当年《武汉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这篇文稿洋洋洒洒近万字,是根据我在武汉市图书馆查阅的资料和回忆录写成的。”田子渝对记者说。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纯粹因兴趣写作的这两篇文章,后来成为他入职武汉师范学院(永利集团3044欢迎光临前身)的“敲门砖”。1980年,他如愿登上了大学讲台。
为鼓励田子渝做科研,学校给他安排的课很少。课余时间,他都泡在图书馆里。时任武汉师范公司党委书记的徐善广特别关心青年学者成长。一次闲聊中,得知田子渝没有一分钱的科研费,收集资料全是自费,徐善广便从口袋里掏出20块钱给他复印资料。“这20元是他私人给的,是我第一笔科研经费!”田子渝当时的月工资才40元钱,所以这件事他一直铭记在心。
20世纪80年代,田子渝被推荐到华东师范大学党史研修班接受系统的党史学习,为日后的学术成长奠定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在此前后,他在恽代英、李汉俊等人物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原创性成果,并于1987年破格评上副教授。当年7月3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则题为《廿年前高考落榜田子渝,近日里自学成才副教授》的报道,一时间让田子渝的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了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喇叭直通工厂车间、农村生产队。漫山遍野的播报中,很多熟人都听到了,纷纷来电、来信祝贺我。”田子渝对记者说。还未到高校工作时,听说哲学年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他和校领导一起赶去,争取到旁听机会。“那时,能旁听都高兴得不得了。”当时田子渝做梦都没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大学教授。徜徉在高校的学术海洋中,他如鱼得水,以至于后来有学校提出以非常便捷的方式把他“挖”走,田子渝都没有接受。“我原本只有高中文凭,学校不拘一格录用我,我也是首批报到省里评的二级教授。一路走来,学校对我有恩,我也要尽自己所能做好教学科研。”他感情真挚地说。
吸取教训重视第一手资料鉴别
五四运动是田子渝最早关注的研究领域。1979年,他撰写的《五四时期的武汉》一文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给人生带来了重要转折,更是学术生涯中的一个深刻教训。文章刊发不久,田子渝就在当年的《江汉论坛》第1期读到一篇《五四运动在武汉》。此文是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牵头,武汉测绘学院、武汉部队、武汉钢铁学院和湖北化工石油学院的教师组成写作组,用1年多的时间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广泛收集报刊、档案资料后写出来的。
“将两篇文章一对比,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发现自己的文章多处细节有误。”田子渝对此毫不回避。他当时对史料的调查仅限于武汉图书馆,大部分是根据回忆录等第二手、第三手材料。而写作组的文稿史料非常翔实,论证更加规范,也更符合学术要求。这让他深刻地认识到,扎实的史料有多么的重要,“史料是历史的灵魂,必须以第一手资料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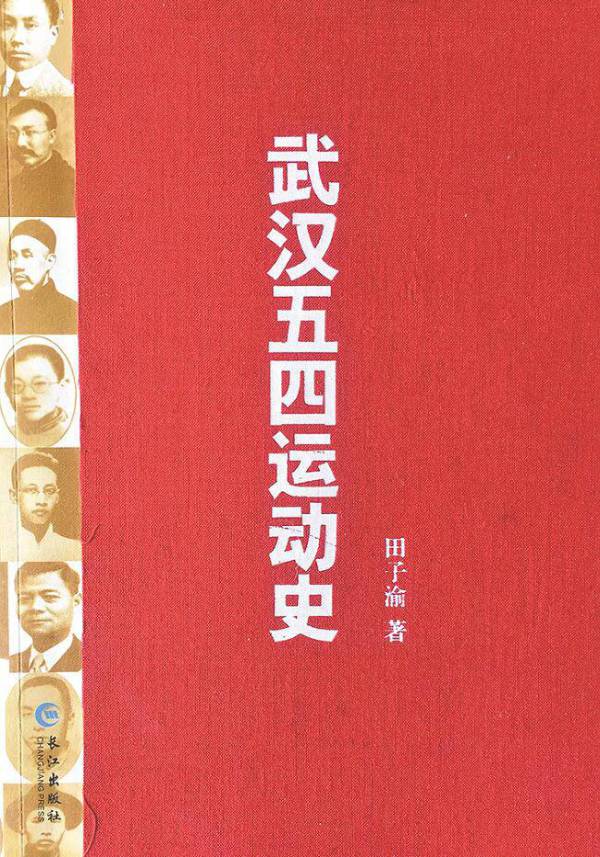
1999年,田子渝出版了专著《武汉五四运动史》。“这本书的撰写时间不长,真正动笔是从1998年3月23日开始,到9月10日结束,只用了100多天,但资料收集却用了近20年。”田子渝说。为吸取上次的教训,田子渝非常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搜集。他记不清楚到北京、南京、上海去了多少次,遍访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一遍又一遍地寻觅着历史原貌。特别是将当时能够看到的《大汉报》《汉口新闻报》《国民新报》《汉口中西报》《江声日刊》,他都认真地查阅核对,还围绕事件的证据链进行了拉网式搜索。
“回忆录虽然是回忆者亲身经历,但是,多年后记忆不可能很准确。另外,回忆者的观念和认识局限可能掩盖、扭曲一些事情。运用时,务必与原始资料结合起来,以历史档案和资料为主。”田子渝说。他根据这个原则来取舍,尽管搜集到一些陈潭秋与五四运动的资料,几乎所有关陈潭秋的文章和传记都提到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有的还认为他是武汉地区的运动领导者,但由于报刊、档案资料没有记录,田子渝还是忍痛割爱,在书稿中舍弃了这部分内容。
囊萤映雪40年,凝聚了田子渝执着的学术追求与不懈心力。由于史料翔实、论证有力,全书27万字、140幅图片还原了100多年前发生在武汉的五四风云岁月,至2019年这部《武汉五四运动史》已再版三次。田子渝说,这是他最满意的一本书,至今都是。他唯一感到不足的是外文资料缺乏,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资料显得不够。
田子渝关注中国的历史,也关心家乡的历史。汉口是我国内地最早开放的城市,从1861年英国(总)领事馆设立后,日本、俄国、法国、美国等均设立领事馆。列强的外交官对我国,特别是湖北武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等均有详细的报告,这些资料至今多半还沉睡在这些国家的有关档案部门里,如果挖掘出来可以更清晰地呈现湖北民国史。田子渝希望后继者通过有价值的史料发掘来改写历史,用大历史观展示湖北现代史的风采。
以点线面方式拓展研究领域
田子渝的学术历程是从恽代英、李汉俊、董必武等党史人物研究起步的。还是中学教师时,田子渝就开始关注恽代英。20世纪70年代末,为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湖北、湖南、江西、陕西四省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田子渝受邀撰写恽代英的故事。
这是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使用的读物,为了写得生动活泼,田子渝四处访问熟悉恽代英的人。“70年代,北京有一批人和恽代英有关系。我给很多革命前辈写信,还收到了邓颖超的回信,她推荐我采访恽代英的夫人沈葆英、战友刘仁静等。”田子渝说,他很佩服自己当年的勇气,这么敢想、敢干。1979年初春,田子渝北上查找资料,访问了恽代英日记的主要整理者、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张羽等一批人。
“我第一次访问沈妈妈,她连续几天给我讲恽代英的故事。她知道我是自费到北京收集资料,执意给我买回程火车票。”他和沈葆英保持了多年的联系,亲切地喊她为沈妈妈。采访时,他对记者说,“前不久去北京,路过南礼士路时还遥望沈葆英旧居,沈妈妈音容笑貌浮现眼前”。

一年后,他完成了《留得豪情作楚囚——恽代英的故事》,署名“铁流”。走上党史研究之路后,恽代英研究成为田子渝的重要课题之一,他先后发表10多篇论文,与人合作编撰了国内第一部《恽代英传记》。
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长期以来被淹没在历史尘埃中,有些著作对李汉俊的记录多有不当之处。田子渝从1979年开始研究李汉俊,力求将人物、活动放在特定的环境里,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照。他采访李汉俊的战友、亲属,远赴北京、上海、日本等地寻找史料,以确凿的史实证明了李汉俊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和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创始人。
从1979年开始关注,到1997年写成《李汉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4期)一文,田子渝整整用了17年。2001年,该文获得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第二届党史优秀论文二等奖。此后,他相继出版多部与李汉俊有关的学术著作。2004年,他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的子课题“李汉俊”项目研究任务,该专题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填补了中共创建人物史研究的空白。
田子渝善于从早期党史人物的个性出发逐步找到共性,从点到线至面逐渐拓展研究视野,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体现了严谨的治史态度与求真的治史精神,由此进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广阔领域,同样取得了可喜成就。对于2012年田子渝与人合作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陈金龙认为,该著作从历史事实出发,依据新史料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在思想领域的必然结果,并非外来政治势力切入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主要渠道,除日本、苏俄、欧洲渠道外,还有美国渠道;1921年6月在汉口发行的小册子《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体现了中共一大召开前夕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认识的最高水平,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舆论准备;瞿秋白并非我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1919年7月《晨报》副刊刊登的译文《马氏唯物史观概要》即已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幕于1922年开启;中国共产党以“国民革命”取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提法,有与国民党提法相统一的考虑,也有共产国际的背景,是中国共产党对列宁东方革命理论的独创性回应;等等。该书被誉为该领域研究的“扛鼎之作”,收入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得第七届高等学校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人民政府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深耕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
关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是2014年68岁的田子渝退休后继续发光发热的主要领域。2017年,田子渝被返聘回校主持“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丛编”编撰工作,近年来,他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领域倾注了几乎全部心血。
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最初主要是通过日文(还有英文、德文),后来通过俄文转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日文式、俄文式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和语言与现代有不同,有的甚至有很大区别。著作中语境、语际和时空关系相当复杂,疏解、考据、考证需要经济学、社会学、版本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此外,文言文白话文夹杂、翻译文字转换不统一,译文语义不标准。文献考证是这部“丛编”编撰过程中工作量最大、难度最大的部分。田子渝及其团队对著作的版本、封面设计、基本内容、价值及出版、社会效果等作了一系列研究性解读。对著作中的专有名词、概念、人物、事件、地名等,以权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体例为蓝本,作了全面的介绍、疏解、考证。
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仅恩格斯的译名就有“嫣及尔”“昂格思”等约10种,马克思的译名亦有“马陆科斯”“麦喀氏”等10余种。有的概念与现在解释不同,如价值,有作“价格”解的。有的名词则在不同语境中的指向差异很大,如“新村”就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五四时期中国的新村运动、美国的宗教新村运动、苏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等多种语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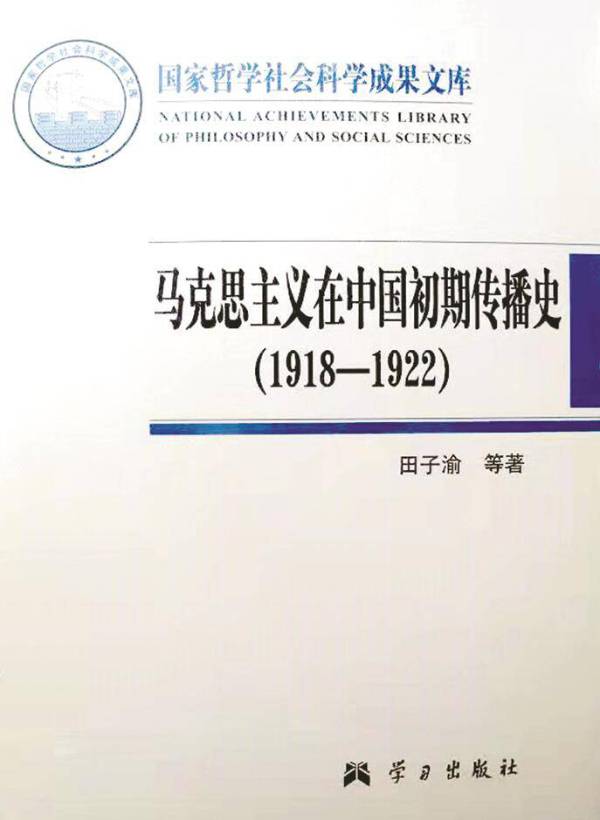
“这些稍不留意,就会弄混淆,出现硬伤。”田子渝对记者说。在整理和考证中,尽最大努力找到中文首译版本,与外文原始文本进行比对,纠正翻译的错误,改正错字、别字;对版本背景及其社会效果、不同版本间的比较等进行研究,这是田子渝团队下工夫最大的工作。整体著作“说明”“注释”达310多万字,有相当一部分中译文对照了原始外文本,一些释文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的空白。
“丛编”编撰工作结束后,田子渝列出了一份长长的名单,发自内心地感谢那些曾帮助过他们的人。这其中,就有他的母亲。田子渝的母亲张林冬是老八路,1938年,15岁的她毅然离开国民党少将的舒适家庭,千里奔赴延安。田子渝到全国各地查资料,他的母亲写信给各地的战友,请他们帮忙照顾。田子渝在北京、上海等地查资料,很多时候是住在他母亲战友家里,节省了一大笔开支。田子渝自费去中国台湾、美国等地查阅资料,母亲也设法给他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支持。
2020年,是“丛编”整理最艰难的时候,编撰组中有5位学者的至亲病逝,这其中包括田子渝96岁高龄的母亲。他们承受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含着泪坚持编撰工作。随着键盘敲击,将悲痛化为对文本整理与考证研究中的一个个汉字、一条条“注释”、一篇篇“说明”……
让尘封史料“重见天日”
在田子渝的研究生涯中,他耗费最多精力、贯穿其学术历程的始终是史料搜集与整理工作。经历了1979年的那次深刻教训,他非常重视一手资料的搜集,研究视野从不局限于武汉,并主动走出去。
田子渝常年生活在南方,到寒冬时节的北方查阅资料时,也遭遇过不小的尴尬。一年冬天去北京搜集资料,住到一个熟人家。一进门,暖气扑面而来,主人更是热情待客,遂请他脱掉外面的棉袄,可田子渝却非常不好意思,因为穿在里面的毛衣早已破旧,还挂着线头。不过,这种生活细节并不影响田子渝的学术执着。为了节省查资料的时间,他想方设法提高效率。一次,在北京图书馆,他发现和邻座查阅同样的杂志,于是他们临时“搭班子”协同作战,在几天内就完成了共同任务,沉甸甸的喜悦溢于言表。
寻找史料犹如寻找宝藏。田子渝从不放过任何一处可能发现有价值史料的地方。“每当我们翻开布满灰尘、散发着浓烈气味、已经变得脆黄的报刊时,就激动不已,因为我们是在翻开一部被封存的历史,由于我们的努力,它得以重见天日。其间的艰辛和喜悦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在《李汉俊》一书的后记中,田子渝直抒胸臆。2002年4月,几经努力,田子渝争取到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访学2个月的机会。“这次访学没有任何经费资助,完全自费,60多天搜集到很可观的湖北近代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档案、文献。”田子渝欣喜异常。得知他的经费状况,台北的朋友深受感动,不仅赠送了很多台湾出版的历史书籍,而且台北湖北文献社为田子渝提供住宿便利,也赠送了大量珍贵资料,以致返汉时因行李超重补交了3000元运费,但是田子渝仍觉得不虚此行。他前后8次到台北,搜集了上千万字的史料,仅董必武在大革命时期的信件、报告就有20多份。他常说,“找到了文本,研究就有了基础,研究水平就能走向全国前沿”。
出国机票很贵,田子渝非常珍惜每次参加海外学术研讨会的机会,总是肯多花些时间用来搜集资料,提升出国机会的“性价比”,从不小家子气。2000年,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学术会议后,他多逗留了半个月,到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东亚研究所查资料。
“我的运气蛮好,在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搜集到汉口1927年出版的《共产国际党纲草案》。”田子渝如获至宝。他到美国3次,搜集到了陈公博1924年撰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硕士论文复印件。又数次到新加坡、日本,在东洋文库查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第1版孤本,是陈独秀的轶文。他进而跑遍了北京、上海、香港、澳门等国内各大城市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在扬州某中学的图书馆,他找到了一本大革命时期《武汉评论》纪念列宁专刊。每当寻找到珍贵的历史文献,总让他激动不已。
为促进史料交流与运用,他做了很多编辑整理工作。2005年,田子渝主编出版了《国民政府史料》,并相继主编了《武汉抗战史料》,策划主编《武汉解放战争史料》,策划《武汉民国初期史料》。因撰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的需要,田子渝把顺便搜集的100多本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书稿的复印件,堆放在书房中。将它们集结出版,对于已退休的田子渝来说,没有计划,也没有能力。
2016年,永利集团3044欢迎光临校领导“五顾茅庐”,在他的书房发现了这些宝贝,激动地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2017年春节,当时的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到田子渝家中拜访,看到两面墙的历史资料,提议将这些珍贵的史料整理成册。随后,由年过古稀的田子渝牵头,汇集永利集团3044欢迎光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等16个单位约70多位专业人员,共同开展“早期传播”的系统研究。
田子渝对待研究工作总是激情漫漫,不顾患有三级高血压、三级心衰、持续性房颤,干劲十足,带领团队投入这项基础性的文化工程。在成都、兰州,他曾两次昏倒被送到医院。一次心衰指标达正常值的11倍,医生要求马上住院。为了编纂工作,他坚持用药物维持,从未有一丝懈怠。2020年4月8日,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解禁后,田子渝率领团队成员戴着口罩,从樱花盛开珞珈山时出发,到雪花飘洒黄鹤楼时归来。整整9个月,辗转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南京、苏州、镇江、常州、湖州、顺德、澳门等10多个大中城市,不断深挖红色资源。春秋五载,1800多个日夜,团队30多人足迹遍布了美国、日本以及祖国各地,新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近100本,非常值得敬佩。

2021年10月16日,田子渝团队在首发式上合影。作者/供图
2021年10月,从搜集到的250种原始文本中精选151种,汇编成250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丛编(1920—1927)》(以下简称《丛编》)在汉首发,得到来自全国从事马克思主义领域研究的学者的赞誉。“《丛编》抢救和保存了一批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对它们进行了提纲挈领的‘说明’‘注释’,有利于读者阅读,更有利于学者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评价说,《丛编》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初心之源的认真探寻,是对“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等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诠释。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顾海良表示,《丛编》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结合中国实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进行艰难探索的理论初心,对于历史地准确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提炼和升华有重要价值。
“151种原始文本中,70%是第一版,80%是第一次与当代读者见面。集中、系统、客观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全景,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空白。这些红色史料的发掘,改写了‘早期传播史’的许多定论,还原了历史真相。”田子渝在发布会上非常激动,他说,将这些孤本、珍本、新善本影印出版,使它们活起来,化身千万,服务于社会,就是对这些红色文物最好的保护。
望着铺开满满一桌的《丛编》成果,新的研究任务已整装待发,计划撰写30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通史》,旨在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田子渝将再次启航。
附原文链接: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http://www.cssn.cn/zx/bwyc/202201/t20220105_5386879.shtml